那些年,为了追随一个城市户口,许多人付出了一生的精力。当一种身份、福利和未来被附着在一张纸片上的时候,这其中被人为割裂开来的差别,从一出生就烙在了不同的个体身上。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与户籍捆绑。此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将户口与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社会福利等公民的权益直接挂钩,由于身份的不同而被设定的不同未来,导致了许多家庭的悲喜命运。
户口故事:被户口捆绑的身份

1958年,被视为中国人口管理制度的一个分水岭。 这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条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一套较完善的户口管理制度。该条例第一次明确将城乡居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种不同户籍,从此,中国步入了一个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
50后:户籍差异人生不同
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付玉玲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因“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年近60的付玉玲生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农村,尽管其父亲是印刷厂的职工,属于非农户口,但根据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婴儿在出生后一个月内须申报出生登记,并随母落户,因而母亲农业户口的性质也决定了付玉玲的户口性质为农业户口。
一纸户口,造就了付玉玲的经历与命运。1957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城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甚至规定“招用临时工必须尽量在当地城市中招用,不足的时候,才可以从农村中招用。”
中学毕业以后,同学中的“非农业户口”可以拥有招工资格,而付玉玲唯一的选择就是返乡。“人家居民户口就招工,你农村户口就别想”,付玉玲用一口地道的关中口音说。
返乡回家后,付玉玲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正是因为结婚,她错过了一个拥有正式工作的机会。“那时候我妹刚从学校出来,正好赶上接我父亲的班。而我刚结婚,错过机会了。结婚以后就出不来了……”付玉玲如是说。谈话中她的眼睛总是注视着远方,与记者少有眼神交汇,似乎在努力回忆着什么。从侧脸看去,她的表情并不多,只有那双文过的眉毛显得异常抢眼,散发着上世纪80、90年代的流行气息。
付玉玲在家排行老四,除了妹妹外,还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家里面唯一有正式工作的就是妹妹,当年接上父亲的班在印刷厂工作,一直到退休。付玉玲的丈夫也是农业户口,年轻时曾当过兵,但回来以后并没有被安排工作。谈起50年代农业户口对其人生造成的影响,她大多数时候都强调的是工作问题,就因为这个身份,她的前半辈子只能在家务农,只能待在农村。
如今付玉玲在西安市的吴家坟公交站牌当志愿者,绿色的志愿者服,红色的帽子,再配上手中红色的小旗,这使得她和她的同事在人群中的辨识度很高。在这里,付玉玲每月可以领到1000块钱的工资,上班时间是上午七时至九时半,下午五时到七时半,每周日可以休一天的假。这份工作她已经干了将近两年,如今马上年满六十,根据规定,她不能再在这里工作了。“人家跟我说了,60岁就不让干了,我再干上几个月就走了”,付玉玲说。
同为50后,李玉的人生经历则与付玉玲大为不同。坐拥城镇户口的李玉,17岁便参加了工作,在西安市某电力部门工作了一辈子,直至退休。“我当时初中还没毕业,上了两年零两个月,单位在我上一届的学生中招工,名额没用完,于是就在我们70届中挑选了一些人去补充这个名额,我就很快很顺利地进单位了。”虽然已是花甲之年,李玉看起来却非常显年轻,烫卷的短发让整个人都很精神。61岁的李玉目前退休在家,和爱人帮儿子儿媳照顾6岁的孙子,安然地享受天伦之乐。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经历,只是因为户籍的不同,却走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60后:三代人的换户口梦
听闻户籍改革政策要实施的好消息,刘运平很激动,也有些许感慨:“愁了多半辈子的事情,政府终于要给我们解决了。”
“辛苦了一辈子,还没能换个城镇户口。”53岁的刘运平无奈地说,一本普通的城镇户口,牵扯着刘运平半辈子的悲喜,也影响着他一家四口的命运。刘运平老家在内蒙古一个经济落后的村子里,他的前半辈子都生活在那里,耕种几亩贫瘠的旱地,一年到头都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
刘运平有个小他三岁的弟弟刘运安,很早就在县城工作,生活要比他好得多。“运安有城镇户口,早些年他家就能分到粮食,我们只能自己种着吃。”看到弟弟生活的改变,刘运平心中早早就有了个坚定的信念:要拿到非农户口。但在农村生活了许久的他并没有好办法,只能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儿子小的时候,我经常教育他,要好好学习,考到城里去,在城里工作并拿到城镇户口,生活就能好得多。”
2010年,刘运平的儿子儿媳怀揣梦想来到西安打工,用自己的积蓄做起了小本生意,渐渐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但他们手中的农业户口仍然给不了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归属感。2012年,刘运平的小孙子蛋蛋出生,给刘运平家平淡的生活带来莫大的惊喜,但也有不少问题随之而来。“儿子儿媳都没有西安当地的户口,当时办准生证特别麻烦,儿子来回跑了三四个月才办好,而本地户口很快就能办好。”刘运平告诉记者,从儿媳妇怀孕开始,家人就为这个孩子的将来做打算,但农业户口的限制使得这个孩子连在城里出生都困难重重。
为了照顾年幼的孙子,2012年底刘运平离开了内蒙古老家,来到西安和儿子儿媳同住。刘运平介绍说,儿子儿媳的店面在沙井村,自己和小孙子住在杨家村的出租房里,两地距离较远。小两口为了省些交通费,平常都住在门店里,周末才回来杨家村一家团聚。刘运平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住的条件不好,但他心里最想要的还是能在西安落户。“儿子一家能定在这里,我就安心了”。虽然现在不再为城镇户专属的那几斤公家粮,但还是希望儿子一家成为真正的城里人。
“因为户口得不到解决,家里好多问题都困扰着我们。”刘运平说。去年11月,刘运平因胆结石住进医院,需要接受手术治疗。住院十多天共花去八千多元,这让本就拮据的刘家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没有西安户口,我们没有医保,看病只能自己掏钱。”刘运平叹着气说,“同病房的病人,出院的时候能通过医保报销一大半,我看着特别羡慕。”
一次手术让刘运平的腹部留下一道疤,也给他心里留下一道印。“还是城镇户口好处多,一定要帮孩子们想办法转成非农户,以后就会少很多麻烦。”刘运平告诉记者,前不久儿子申请到了居住证,这是他今年最高兴的事。“有了居住证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廉租房,我们全家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说到这里,刘运平的脸上充满笑意。他告诉记者,居住证是他们走向城市的第一步,小孙子渐渐长大,不久就要面临上幼儿园、上学的问题,自己慢慢变老,也需要一些社会保障措施的扶助,而一个西安市的户口会让这一切变得顺利。
听闻户籍改革政策要实施的好消息,刘运平很激动,也有些许感慨:“愁了多半辈子的事情政府终于要给我们解决了。”有了好政策,刘运平一家将会享受到一些城镇居民的福利,刘运平期待孙子蛋蛋可以得到很好的教育,一家人都享受医保,就像他说的“很快就能成为真正的城里人,日子越过越好”。
70后:命运被商品粮改写
一个吃商品粮的梦想,将张夏的未来定格在了乡镇。如今他10岁的儿子,又开始了像他一样的奋斗历程,只不过这次不是户口,而是城市。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帷幕,刚刚走出十年浩劫梦魇、百废待兴的华夏大地吹来第一缕春风。
198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颁布,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通知规定,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并同集镇居民一样享有同等权利,履行同等义务。
1985年7月,《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的出台,标志着城市暂住人口管理制度走向健全,公民开始拥有在非户籍地长期居住的合法性。同年9月,作为人口管理现代化基础的居民身份证制度颁布实施。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户籍相联系的一系列户籍权益逐渐调整而呈现出弱化的趋势,户籍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和制约也大大降低。1992年底,国务院宣布自1993年1月1日起在全国放开粮油市场价格,停止粮票流通,户口与粮油挂钩的历史至此宣告终结。随着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农民也有机会通过高考改变自身的命运。
对于70后来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在实际利益上的不平等,已经呈现出逐渐弱化的趋势,但两类户口所衍生出的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依然在一些人的身上留下了烙印。
对于户口和身份,生于1976年的张夏,有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事情。
那是一个春天的中午,他和父亲从地里干活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镇上的同学和他的父亲拉着一架子车的粮食从粮站回家。车子上的粮食堆得很高,有当时颇为稀缺的白面和大米,还有各种杂粮。他问父亲:“我们为什么不从粮站买粮吃呢,在地里累死累活干一年,也不过就打那么点粮食。”他父亲告诉他:“那叫商品粮,不是谁想买就能买的,有城镇户口的人才可以拿着粮本去粮站买粮,我们是农民要吃粮就只能种地,你要是不想种地,那就好好学,考个身份当干部!”张夏就是从那天开始,认识了户口对于一个人命运的重要性。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张夏从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考出农门,换个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
正是因为这个梦想,张夏发奋苦读了三年,在初中毕业的时候,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所中专。他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告诉父亲,他考上了,有工作了,以后就可以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也可以有粮吃了。当时以张夏的成绩,其实完全可以上一所好的高中,读三年考个好大学。但是因为家里条件差,还有两个弟弟妹妹,所以张夏压根就没想过继续再读高中,而是满足于自己终于有了干部身份,有了一个城镇户口。可是让张夏始料未及的是,等到1997年他中专毕业的时候,一纸中专文凭已经完全在这个发展飞快的社会上没有了立足之地,用张夏的话说“几乎和文盲没什么差别”,后来费了好多周折,找了好多关系,终于被安排到老家一所小学工作。
经过工作后的继续进修,张夏拿到了大专文凭,如今在一所乡镇中学当老师的张夏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掩饰不住的却是酸楚,“当年和我一样学习最好的一批学生,上了中专,毕业后大多分配到家乡工作,而当时学的一般,考不上中专只能上了高中的这批人,现在大部分都上了大学,有些在省城工作,差的也在市上,比我们有了更好的发展空间和平台。其实当时如果不是心里揣着一个吃商品粮的梦,也许我可能会选择上大学,或许会比现在有更好的成就。”
一个吃商品粮的梦想,将张夏的未来定格在了乡镇,如今他10岁的儿子,又开始了像他一样的奋斗历程,只不过这次不是户口,而是城市。(记者 贺小巍 实习生 李蕾 崔睿娜)
户籍制度,本质上是一种人口登记管理制度和人口分布调节机制,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实现人口的有序管理。近年来,户籍制度之所以饱受诟病,在于其身上附着了太多的社会资源和社会福利的分配功能,很多人被一纸“农业户口”剥夺了诸多的福利。
户口故事:被户口剥夺的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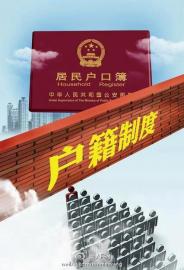
作为国家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户籍制度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实施。
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涉及到就业权利、教育权利、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各个方面。同时,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快速发展,户籍制度逐渐成为了隔绝城乡、区分人们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标志,造就了公民福利待遇的不平等。
田辉:孩子啥时能来到我身边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长大成为栋梁之才”,上一所名牌学校,拥有优秀的师资力量和良好的教学环境,自古以来是中国家长对孩子学习和学校教学的期许。
新的一学年即将开始,可是,在西安打工的田辉夫妇近几天却一直在发愁:“孩子上学怎么办啊?”原籍宝鸡市扶风县的田辉夫妇,在西安市长安区做饮食生意已经有四个年头了,因为二人常年在外做生意,八岁的儿子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但田辉夫妇却不由地担心:“孩子本来就调皮,而且村里的教学水平也不是特别好,老人也没有多少文化,不能辅导孩子的功课。现在孩子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所以就想把孩子转到西安来上学,一来西安的教育水平高,二来在我们身边也好看管。可是我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根本不接收农村户口的孩子。”
记者联系了西安市几家小学,正如田辉夫妇所说。据西安市新城区中兴路小学自称值班人员说:“我们学校今年计划招收学生数额已经满了,在6月15日已经给符合条件的家长打过电话了,6月20日,家长们也都来学校登记过了。”据记者得知,值班人员所称“符合条件”包括招收学生户口要符合学校要求。
据记者调查,除中兴小学之外,西安市莲湖区龙首村小学等同样对户籍有限制。龙首村小学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学校没有名额了,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太多,而且入学必须是学区户口。”
2012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公办小学、初中是接受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的主渠道。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就学必须提供“四证”:一是其父母的身份证明;二是公安部门办理的本市暂住证;三是户籍所在地区县教育局或乡镇政府同意其出外就学的证明;四是父母从业证明或用工合同。
然而,目前某些学校对户口所在地的限制仍然存在,只有拥有学区户口才可入学。这不仅对城市里部分非农户口的学生有所限制,对所有的农业户口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2014年7月30日《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公布,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同时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纳入各级政府教育发展规划和财政保障范畴;逐步完善并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和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政策以及接受义务教育后参加升学考试的实施办法。
“如果新的户籍政策的出台可以使学校放开户籍限制,让我们农村的孩子也在城里上学,那样不仅可以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也可以使孩子呆在父母身边。”田辉夫妇很是期许。正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学专家石英所说:“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下一代的流动将定居下来,最根本的是通过新型城镇化保证未成年子女尽可能多地和父母在一起,通过户籍、就业等政策使未成年子女随父母一起走。”
刘琳:啥时也能申请保障房
近日,西安市高新区某房地产销售顾问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户建筑面积89.52平方米的二居室,单价已高达8011元,每平方米折后价为7011元,折后总价达627621元。首付30%即188287元,贷款则需439336元,即月供3218元,需要20年能还清,或月供2732元,需要30年才能还清。
对高额房价,在西安市某私企工作的刘琳对此发表感叹:“事实上,房价真的太高了,也许城里人可以接受,但是,对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在西安立足啊。”
西安市户县人刘琳,四年前,和男朋友留在西安一起奋斗事业,眼看就要结婚了,可是目前还居住在雁塔区鱼化寨月租300元的城中村里。“去年,我和男朋友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想着能不能在西安申请廉租房。可是,经过一打听,要满足多个条件才可以申请,首先就必须是本区非农业常住户口,但我俩都是农业户口,这一条就打破了我们的愿望。”
据刘琳了解,申请廉租房除了户口的限制还必须符合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17平方米且为失业下岗家庭或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540元,包括区民政部门认定的城镇低收入家庭在内的生活特困难家庭,且符合城镇低收入家庭条件的优先照顾。同时还要提交书面申请书,民政部门出具的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证明或政府认定有关部门或单位出具的收入证明,申请家庭成员所在单位或居住地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现住房证明等一系列证明。
而近期出台的《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让刘琳实为欣喜,她表示:“我们因为户口,城里的很多福利都与我们无关,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我们可以成为非农业户口,这离申请廉租房也就进了一步。户籍改革,是不是意味着我们距离解决住房问题就进了一步?不管能不能申请到,政策是好的,最起码我就可以享受一些城市人的福利了,这也说明政府也越来越关心我们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事啊。”
刚刚参加工作的杨碧云为此也深表喜悦:“农业户口确实在某些方面限制了我们的选择,而户籍改革对于我们将要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应该是值得欣喜的。首先,我们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待遇了,长远考虑,对将来住房、孩子教育等都会有保障。”
户籍改革的最终目的不仅是还农民以迁徙的自由,给农民与城镇居民相等的权利,更重要的是使他们获得自由发展的可能,赋予他们与城镇居民竞争的能力。正如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农村所所长王建康所说:“过去的户籍制度,将城乡居民分割开来,很多人因被农业户口剥夺了某些权利便付出很大的代价去改变它。而这次的户籍改革,是一次具体的、系统的改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逐渐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
张全生:期待“市民待遇”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社会转轨时期,进城的打工者大批涌入了产业工人的队伍之中,成为产业工人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省二季度农村外出人员已达到506万,近七成劳动力二季度末选择在省内务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市之中,但他们的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在现有的户籍管理体制中举步维艰,成为城镇生活中的边缘群体,过着候鸟式的生活。
由于身份的限制,打工者主要集中在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的“苦、脏、累、险”行业,他们工作条件苦,收入水平低,居住环境差,未被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很难享受到正常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他们为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游离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得不到基本的身份认同,长期以来被无情地拒之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
“如果我是非农业户口,情况是不是就能好一些,最起码我能享受到一些社会保障和福利。可是现在我什么都做不了,事情暂时只能这样被拖着。”张全生感叹道。
张全生,西安市周至县某乡镇居民。2014年1月8日,张全生因在周至县城某工地打工时出事故,小腿部伤残断裂,被西北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为“六级伤残”。“当时事故刚发生,工地负责人将我送到周至县医院进行治疗,但因为伤势特别严重,只在县医院进行了简单包扎就被立刻送往西安红会医院,最后工地再无人过问,我现在连工地的负责人都找不到了。”张全生告诉记者。
据悉,住院期间,工地负责人支付了4.5万元医疗费。其后,张全生三次前往西安红会医院进行复查又花费4000余元,后向用人单位索取工伤赔偿,工地负责人却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为由拒绝。
“事发后,我第一次去找工地负责人寻求赔偿,负责人说告诉他一个赔偿额就可以进行赔偿。第二次工地法人不仅不能按照工伤赔偿,还将赔偿数额一降再降,后来就互相推脱责任。到现在负责人电话打不通,人找不到。大半年过去了,我的腿还没有恢复,现在只能在家呆着养伤。”张全生无奈地说。
目前,和张全生一样的打工者迫切希望得到公平的待遇:“作为一家的顶梁柱现在成了六级伤残,以后的生活该咋办呀!我在想,如果我们是非农业户口,就不是现在这样了。比如,如果我要申请低保,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也在保障水平上会有很大的差距。”(记者 康传义 实习生 李岛)
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二元制户籍政策把我国人口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也把两种人的生活设置成完全不同的两个模式。如今户籍管理制度改为一元制,我国农民的身份将被重新设置。这让他们感到欢喜,对于明天有了更多更美好的期待。
户口故事:被户口设置的未来

伏旱过后一个凉爽的雨天,25岁的青年张立山走向雨雾中的西安火车站售票厅。终于,他做了这个决定:退掉那张回家的车票。
四年前来到西安求学的张立山,至今因为无城市户口,在工作和生活上屡屡受挫。前不久,面对重重压力手足无措的他考虑再三,决定回家。
7月底,国家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我国将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的区别,二元制户籍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逐渐建立居住证制度,推进新型城镇化。张立山改变回家的决定,正是因为这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的出台。
像张立山这样居住在城市里,但得不到城市户口的“城市漂流者”全国有近两亿人,这次户籍制度的改革,无疑是为他们的城市梦插上了翅膀。户口问题即将得到解决,他们也开始重新对自己的梦想规划,对以后的人生也有了新的打算。
我想在城里有个家
相比张立山,大学毕业两年的钱俊峰就要幸运得多。2008年,作为全村唯一一个考进一本院校的学生,钱俊峰满怀期待和憧憬来到西安。临行时,钱俊峰告诉父母,他要在西安工作,将来把二老接到城里过好日子。
2012年,学完四年兽医专业课程的钱俊峰毕业,但面对人才市场的火爆,找到工作并非易事。几经周折,他进入一家小型宠物医院工作。但离开了学校,他却难觅一个栖身之处。仍然拿着非本地农业户口的他,不能申请廉租房,但市面上出租的房子价格偏高,这让薪水微薄的钱俊峰只能望洋兴叹。幸运的是,宠物医院的老板答应小钱可以住在店里,顺便帮忙照看店面。“我买了一张简易钢丝床,支在库房的狗笼子旁边,就那样住了多半年。”提起那时的困境,钱俊峰脸上充满苦笑,“但当时我已经挺满意了,这比我之前找工作时住的环境好多了。”他告诉记者,他租住过四五平方米的小隔断间,地方小的只能容下一张床;也住过没有小天窗的地下室,气味难闻且有老鼠和蟑螂。“就是这样的房子,每月都要二三百元。可是当时我一没工作二没西安户口,又有什么办法呢?”钱俊峰无奈地说。
2013年,每月工资不到两千元的钱俊峰决定转行。“我的那点工资刚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要接爸妈来西安太难了。”当年9月,钱俊峰依靠自己闲余时间学习的电脑制图技术,找到了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作,进入新媒体行业。不久,因为得到公司领导的赏识,钱俊峰的薪资水平提高了不少,他结合自己的经济情况,在茶张村租下一间月租金600元的房子,开始了独居生活。“虽然离工作地比较远,条件也不怎么好。但价格比较低,我也算有个家了。”钱俊峰腼腆地笑着,“但我还是希望能享受到条件好一点的廉租房。”
苦尽甘来,因为户口问题一直在为住房发愁的钱俊峰终于盼来了希望,今年7月底,国家出台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钱俊峰第一时间看到了这个好事情。“真的很激动,我仔细地看了《意见》里的内容。”他说,“国家逐步放开大城市落户限制,我可以先申领常住户口了。”钱俊峰告诉记者,有了常住户口,他就可以申请公租房、廉租房,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据了解,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让在城镇就业居住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暂时没有落户的,能够逐步享受当地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一目的,对于千万像钱俊峰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堪比雪中送炭。
“我感觉我的未来充满希望,我得好好规划一下我以后的生活。”钱俊峰很高兴,他告诉记者,如果政策落实,他最要紧的事就是申请保障住房。“最好能申请个面积稍微大点的,这样我就可以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了。”钱俊峰告诉记者,有了户口他不仅能享受到住房的优惠,在医疗、社保等许多方面都能享受到西安本地人的福利。
钱俊峰告诉记者,他很想长久地留在西安,《意见》的出台让他的工作热情高涨,生活的积极性大大提高。“这个政策是真的好,它让我在西安能生活得更容易些。我越来越爱这里了。”
农二代的上学梦
新户籍改革制度的出台,不仅给外来年轻人带来希望,更为常年生活在城市里的外乡人给予政策上的支持。租住在李家村的李良才心中一直有个郁结,但最近他的心情好多了。8月13日下午,晚饭时间刚过,李良才赶紧抽空拿出手机,给远在陕北老家的妻子和女儿打电话。接通电话的他显得格外开心:“喂,丹丹,你可以来西安上学了!可以和爸爸一起住了!”
35岁的李良才是个厨师。十年前,他的父母相继过世,为了更好地生活,李良才和妻子离开陕北老家,来到西安打拼。夫妇俩有一个可爱懂事的女儿丹丹,一家人在西安生活虽然清贫,但也和乐融融。
2013年9月,年满7岁的丹丹应该步入小学,但西安一些学校的大门并没有向她打开,因为她远在陕北老家的农业户口。李良才告诉记者,他们夫妇俩跑遍了附近的小学,好一点的学校不愿接受外地户口的孩子,而愿意接受孩子的学校,不是收费高就是离家太远。几经考虑,李良才决定让妻子带丹丹回老家上学。“我工作忙,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李良才说,“谁都知道西安的教学质量高,但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回老家念书是个无奈之举。”
据了解,本次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另一大目标,就是要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益、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农业户口外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就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听闻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可以解决孩子异地上学的问题,李良才赶紧给妻子打电话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同时,他的心里对未来有了无限憧憬。“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丹丹能在西安上学,我们一家能在西安团聚。”李良才告诉记者,一个人在西安工作忙,回家也没人问候,感觉很孤独,自己也很挂念远在陕北的妻儿。他表示,如果孩子能在西安上学,就能受到更好的教育,对孩子的发展很好,以后考大学更容易些。
“远一点说,我想把家就安在这里,不想再回农村了。”李良才说,老家土地贫瘠、经济条件落后,生活条件不好,况且也没什么亲人了。如果孩子的教育问题能在西安得到解决,他会鼓励妻子也在西安找份工作,长久地留在西安。“如果《意见》实施,我们还可以享受到许多城里人才能享受到的待遇,也不用纠结自己的农业户口了。”李良才脸上满是喜悦的笑容,他对记者说,西安城市大,整体生活条件好,他希望从自己这一代做起,真正从农村走出来,让自己的后代都成为城市居民,享受到城市的基本公共教育、医疗、文化和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城镇户口的实惠。
本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创新人口管理”,其中不仅包括众望所归的对农业转其他户口人员的基本保障,更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缩小了城乡户籍的差异,扩大了基本社会公共服务的覆盖面。这对于众多“人户异地”人员的生活具有莫大的帮助作用,也是我国推进城镇化的有力举措。这正如李良才所说,“我们不再担心农业户口的限制,也不奢求非农户的‘小红本’了。”
做个创业的城市居民
“有了新的户籍制度,我离梦想就更近了一步。”在八里村一家汽修店工作的康平师傅高兴地说。康平的梦想很简单: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汽修店。但在原户籍制度的约束下,他想实现梦想有太多的困难。
36岁的康平,来自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初中毕业后,为了能尽早赚钱贴补家用、供弟妹读书,一直对汽修感兴趣的康平外出求学,来到宝鸡一家大型修理厂学习。三年后,康平学成出师,来到西安开始了自己踏入大城市的第一步。这一干,就是十多年。
十几年间,康平娴熟的修理技能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被众人所赏识,康平从最初工作的小修车摊走到了现在的大型汽修店,他的薪资水平也随之有所提高。渐渐的,康平不再满足于给别人打工,萌生出了开一家自己的汽修店的想法。首先,要有一家店面。2012年,康平看中一个铺面,想租下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但自己缺少资金和技术,又是非本地农业户口,这让他一开始就吃了闭门羹。“当时我只能付得起店面三个月的租金,可是房主要求一年起租。”康平说,“况且我自己也缺乏技术知识,尤其是车上的电脑系统,导航这些。”于是,康平的梦想被搁置,他只能以一个外来务工人员的身份,继续打工。
但最近,国家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使康平想开一家汽修店的想法,又有了实现的可能。《意见》中指出,本次户籍制度改革的一个方向,就是倾向于农业转移人口。政府应全面提供相应的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并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康平告诉记者,此次《意见》的出台,自己终于能摘掉农业户口的帽子,也可以申领居住证,这是他开店的一个大好事。“取得居住证后,我就可以享受政府的免费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了。”康平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还可以享受到城镇创业扶持政策。这样一来,我的店就有希望开起来了!”康平随即找到他所在的雁塔区相关部门,就创业一事进行了咨询,并且去了银行咨询贷款事宜。得到肯定答复的他,又开始寻找一个地段好的铺面。康平告诉记者,来西安这么多年,因忙于挣钱养家,他一直漂泊在外未尽孝道,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城乡户口的差异也会逐步取消,他也想让父母感受到平等的幸福。“我父母始终觉得自己是农民,就低人一等,现在户籍都一体化了,应该也接他们来西安,过过城里人的生活,感受一下政府户籍制度的人性化。”
户籍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基本制度,户籍改革联系着万家灯火,关乎国计民生。此次《意见》的出台,以消除城乡户籍的差别为目的、以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内在要求,逐步融化二元户籍制度在人民群众中造成的坚冰。对于像康平这样的农业户口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这项举措虽然刚开始实行,却给全国将近一亿人带去了希望和圆梦的可能。
过去的二元制户籍政策把我国十几亿人口分为两种,也把两种人的生活设置成大体相同的两个模式;如今户籍管理制度改为一元制,像康平这样曾经受户口影响的“城市漂流者”们,又被重新设置。只不过,这一次让他们欢喜,并给予他们的未来诸多美好的期待:钱俊峰期待着住进便宜舒适的公租房;李良才期待着能让自己的女儿在西安上学;康平期待着自己汽修厂的开业……他们都期待着在城市里握紧稳稳的幸福。(记者 刘锦 实习生 崔睿娜 郑宝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