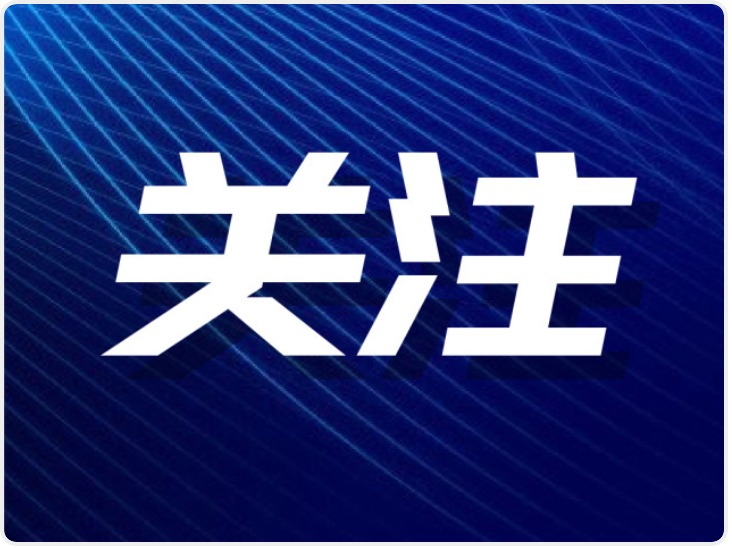8月7日,西安市安东街,一个裁缝正给客人缝制床单。她说:“虽然累,但收入还不错。”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月入3000元,上午10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有事可随时走……张玲的工作性价比就是这么高,但她并不看好这行业的未来:年轻人都不找裁缝了。
师傅的四个徒弟只有她出师
昨日,西安的早晨凉风飕飕,上午10点,张玲的店门口客流不断,“这个裤边你给我裁一下”,“收收腰,别显肚子”,“大姐你看我这裙子能改短不”……她生意好,记者等了半小时,见张玲手头稍歇,才上前搭话。
张玲今年43岁,合阳县新池镇人。1986年西安田家湾技校去合阳县开课教裁剪,镇政府组织了一帮大姑娘小媳妇去培训班学艺,张玲是其中一员。
“当时每月工资才多少钱。”她说,这次技校来授课,普通裁剪班要上两个月,每月学费30元。张玲想到,母亲每次做衣服都要求人先裁好,才拿回家继续做,她就决心去上裁缝班,“我学会了,这个事就我承包了。”
两个月课上完,张玲又认了一个在部队被服厂干过的师傅,跟她学裁缝实践。有天张玲睡不着,干脆起来锁边、钉扣、熨烫……一晚上收拾了8条裤子,然后整齐挂成一排。第二天师傅一见,赞不绝口,“你这样的学手艺,能成!”
师傅带了四个徒弟,其他人对这个行业不看好,最后只有张玲出师了。
工作自由别人转行她“坚守”
谈话间,来了一名穿白短袖、蓝色牛仔短裤的女孩,她要求张玲处理一件上衣,态度不算友好,张玲找个理由拒绝了她。“这种客人,我不想接待。”张玲说。
对制作成衣的要求,她也觉得不划算:“一条长裤三十,一件上衣五六十,费工夫不说,钱也挣得不多。”
仅昨日上午10点前后的半小时,就至少有10人来交件或取件。裁裤边5元,补裆10元……虽然张玲一直没透露自己的平均月收入,但以每件收10元,每日20件,每月25个工作日计,她的月收入约5000元。张玲说,总的来说,收入一直在上升。“以前裁裤边两块,现在五块。”她又说:“啥价不涨?那会儿胡辣汤一块五,现在也五块了!”
“真有急事了,又没顾客急着拿衣服,我拉闸门就走。”对于工作自由度高这个很多人羡慕的好处,张玲却觉得“太自由了”。
为儿子上学,张玲和丈夫于1997年来到西安,在大学南路租了房,继续做裁缝。“那时大学南路还是自由市场,卖丸子汤的、卖菜的、卖衣服的都有。”昨日,70岁的大学南路老住户张建国说:“裁缝也多,有六七个。可张玲手艺好,人也有耐心,好多人找他。”
张玲记得,那时一条街上的同行,以“南方裁缝”居多,其中有四川人,也有江苏人。后来,随着大学南路市场改造,这些同行陆续搬离或改行,现在大学南路街面上的裁缝,只剩她一个。
裁缝店转型难年轻人不愿学
然而,不光裁缝选择改行,选择入行的新手数量也在下降。1989年,张玲在新池镇开的裁缝班,来了25个学生,最后一个都没进入裁缝行业。
昨日,记者致电陕西华山技师学院。一位老师说,学院租用的土地和校舍确系原“田家湾技校”所有,但“田家湾技校”现在什么状况,这位老师并不了解。多位省内外职业学校的招生老师告诉本报记者,近年来,服装专业招生源数量不断下降。
32岁的陈女士说,她的母亲“每件衣服都是裁缝做的”,但她自己的衣服,全从服装店里购买。“论速度,我们哪能比得过服装厂?”张玲说,她的成衣客户也是以中老年人为主。
住在张玲店铺附近的年轻男性,鲜有来找她缝补衣服的。张玲认为,如果这种趋势不能被扭转,裁缝业难免一天天衰败下去。
从业25年的裁缝周师傅说,街边小店的裁缝都想“转型”,但不知从何下手。“我觉得市民还是需要裁缝,可是他们找不到我们,我们也找不到他们。”他说。
社区记者武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