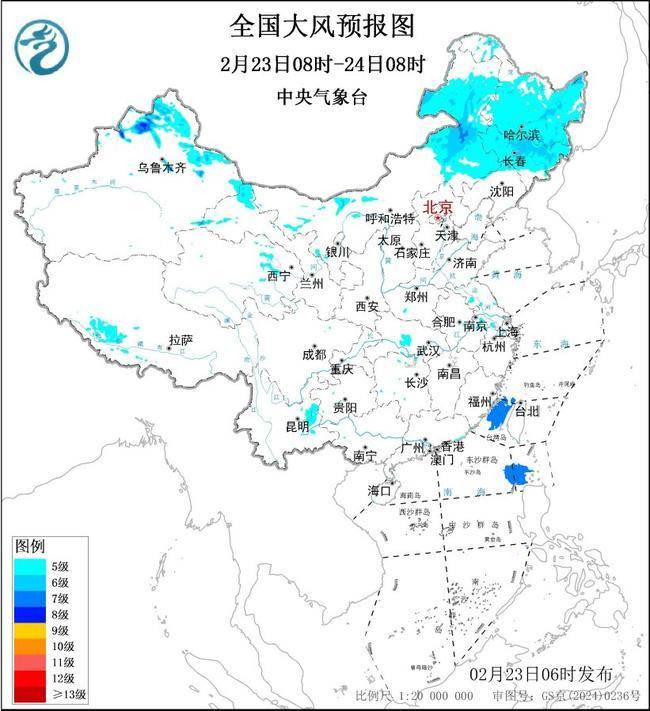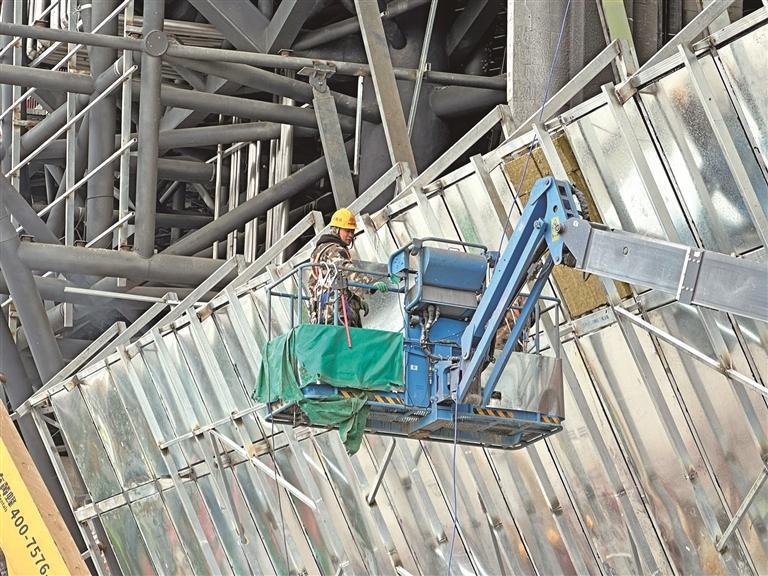各方说法
>>医学专家
艾滋病患者在浴室不会传染
北京地坛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医师伦文辉表示,经过研究,健康人与艾滋病患者日常生活中不仅交谈、吃饭等不会被传染,进入公共浴室、游泳池也是安全的。
伦文辉说,一方面通过科学研究告诉大众不会被传染,另一方面又要限制艾滋病患者,这是不合理的。他指出,艾滋病病毒很脆弱,一般来讲脱离体内很快就会死亡。公共浴室肯定有一定的消毒措施,并且洗澡的水温也容易加速病毒死亡。
从现实层面讲,伦文辉也质疑其可操作性。伦文辉指出,首先艾滋病是看不出来的,必须经过科学的检测。这项规定如果施行,是否意味着每个人去浴池前都必须先检测是否患有艾滋病?
伦文辉指出,即便出台政策的目的是保护公共安全,艾滋病患者也需平等对待。两者之间的平衡需要以科学为依据。
修脚搓澡有风险建议分级管理
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系教授王月丹认为,“这个规定是针对整个洗浴行业的,除了淋浴和泡澡,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创伤的服务项目,比如修脚,用修脚刀的时候可能会对皮肤有损伤、流血等创伤现象,这个其实有可能是会传播HIV的。再比如搓澡,有些人用力比较大,可能会导致有毛囊炎的人皮肤破损,可能会有传播风险。从医院管理角度来说,凡是接触过HIV感染者体液的物品都是要按照医疗垃圾来处理的。”
王月丹表示,禁止艾滋病患者进入公共浴室,是出于对大众健康的保护,而非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王月丹建议,可以对洗浴行业分级细化管理。“如果这个地方只是提供泡澡,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不用挂警示的标志;但是如果涉及到修脚、搓背等服务的地方,那就应该有警示的标志。”
>>法学专家
专业问题应由医学专家论证
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表示,艾滋病患者进入公共浴室是否会传染,这是一个专业技术性的问题,应该听取相关医学研究的医生、专家的意见,“邀请多位医学专家,尤其是在艾滋病领域的专家,进行严谨的科学论证其风险和必要。”
姜明安说,法律条文制定中有一个“比例原则”,风险大就应该制定法律,而风险小则可以不写进条文。“打个比方,艾滋病患者可能会在浴室中与人发生摩擦,冲突中患者咬伤了某人,导致其感染”,但是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如果通过立法的方式来降低这种很小的可能性,那么成本就太大了”。而如果通过专家学者论证,艾滋病患者进入浴室共浴之后,传染率非常高,“即使100个老百姓中,有99个都同意他们进入,也是要立法禁止的”。
姜明安认为,国务院法制办在征求意见办法的同时,应该邀请一批医学专家开会论证,最后出一个论证意见,再进行法律条文规定的制定。
>>防艾人士
病毒含量低可忽略不计
国内首位在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认为,该规定“很荒唐”,说明中国在艾滋病防治教育方面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
张北川以1988年奥运会跳水冠军洛加尼斯为例。洛加尼斯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在比赛中曾受伤,血液流到泳池中。赛后,有学者出面表示,通常比赛选手不会被传染艾滋病。游泳池和浴池相似,含有病毒的血液在水中必须要达到一定浓度,受传染者身上还必须有新鲜伤口,才可能造成传播。
张北川介绍,去年我国有1000多名医务人员直接接触艾滋阳性感染者,例如被艾滋病患者使用过的针具扎伤,但无一人被感染。一般情况下,针具感染的概率是三百分之一,一次性交感染的概率为千分之二左右。浴池中艾滋病毒含量远远低于血液和精液中,传染的可能性可忽略不计。
今年8月,英国政府宣布,从明年4月1日开始,英国艾滋阳性医务人员解除禁止从事外科手术禁令。在该种情况下,再考虑浴池水感染的问题,完全没有必要。
张北川强调,如果该条规定最后实施,会强化公众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
引起公众误解导致歧视
北京最大的民间艾滋病防治机构淡蓝网CEO耿乐表示,他们昨天上午还就此事开会进行了讨论,认为这项规定存在论证的缺失,“可能没有与疾控、卫生部门进行沟通”。耿乐表示,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公共浴池或者大浴池,并不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但是因为这项征求意见的出台,可能会引起“公众的误解与恐慌”,从而导致对于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歧视。
“我们已经给商务部网站征求意见的信箱发送了邮件,提出了我们的建议”,耿乐希望政策正式出台前,能够征求一下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