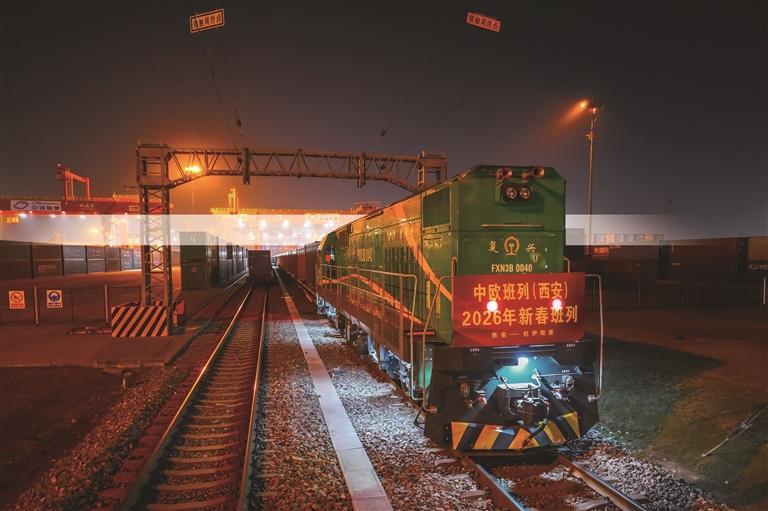相互拆借救火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啊,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府谷县一名苏姓煤老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目前大多数煤老板为了不影响信誉评级,脑袋里想的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想方设法先把银行到期的贷款还上,“都是我一块、你两块、他三块地相互拆借'救火'”。
但现在处在旧历年关时期,许多贷款到期了,按民间习惯,年底都要把账务清算一下,“找钱更难了,面对银行还款的压力,还银行贷款现在也难以为继了。”苏老板说,“不停倒贷”也让煤企不胜其烦。
2014年1月7日,时代周报记者在神木县、府谷县境内的一些煤矿货场内看到堆积如山的煤炭,仍有一些拉煤的货车来往穿梭在路上。实际上,这些煤炭大多来自于国有煤企。
某国有大型煤矿一名高管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国有煤矿不管市场行情怎样都要生产-国企要正常执行重点计划,要设法完成产值、销售收入等经营指标。
此前多年,由于高需求、高回报,致使煤炭产业的投资异常疯狂。为了改善煤炭产业生态环境,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安全性的目的,陕西启动了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在重组整合中,各煤矿股份在二级市场流转频频,一些私营煤矿主不惜背负高利贷在高位进入,接下来遭遇煤炭市场忽然来临的“冰河期”,这些煤矿主的债务因此雪上加霜。
2010年9月,陕西启动大规模煤炭资源整合,按照计划,第一阶段目标是到2011年6月底,通过煤炭企业兼并重组,使煤矿开采主体从550家减少到120家以内,煤矿数量减少到400处左右。
在陕西煤改的强力推进下,榆林和延安等地在煤炭资源整合中要求煤矿企业必须抛弃以前广泛使用的炮采,上马综采设备。此举虽然令煤矿生产的安全性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其技术改造和购置设备费用庞大。
据业内人士介绍,煤矿技改,每吨生产能力的投入在500-700元,即一个年产90万吨的矿井,最少需投入4亿多元。
根据陕西煤改计划,煤矿扩产建设和技术升级改造将按设计分步实施改造。但是,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部分机械化矿井出现成本售价倒挂,综采成本每吨达到100元,煤矿效益陷入亏损。
业内人士称,在陕西参与资源整合的主体煤矿的私营矿主均负债率高企,榆林当地的一些煤老板背负了少则数亿多则一二十亿元的债务,其中除了来自民间融资,还有来自银行的贷款,“光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就高达七八亿元”。
煤企糟糕的经营状况,使煤老板的偿债能力下降了,已经引起商业银行的警觉。神木、府谷多位煤老板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一些商业银行回笼资金后,尤其收紧了对民营煤企的贷款,基本不再往外放贷了,民营煤企进一步融资困难很大。而一些摊子铺得大的私营煤企在展开技术改造中资金链已经断裂。
府谷县庙沟门一名王姓煤老板对时代周报记者称,自己和另一个合伙人将年产30万吨的煤矿整合为90万吨,前期投资7亿元,现在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阶段,至少还要投资4亿元。因为没有产出和收益,融资目前还找不到门路。
2013年,神木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断裂,连续爆发多起民间非法集资大案,标志以煤炭产业为投资主体的民间信贷崩盘,其中煤老板“跑路”事件不断。因煤炭资源整合,也引发了民间借贷方面的纠纷诉讼,有人将其称为“煤改后遗症”。
据榆林当地一位媒体记者透露,目前当地多名煤老板在煤矿资源整合期间,因为涉嫌民间非法集资案而被警方刑拘,有的将面临公诉。不少煤老板在完成煤炭收购、资源整合后,因为技术改造资金无法筹措到位,只有放弃,非常可惜。
有媒体报道,煤炭市场的变化让陕西煤改的实施横生变数,计划中的煤矿建设升级大潮并未来临,改扩建陷入资金僵局。
“在现在这种市场情况下,让煤矿花巨资建设机械化的矿井,很多人真的不敢再往里冒险了,但政府主导的煤改有点'一刀切'的味道,应要兼顾到拯救煤企。”榆林市横山县一位民营煤企老板对时代周报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