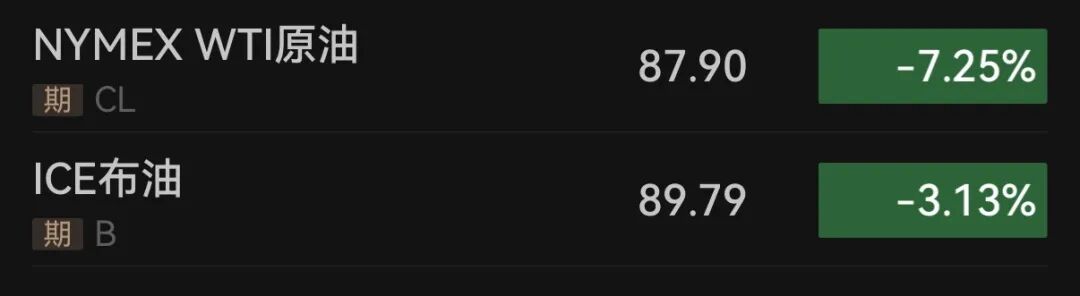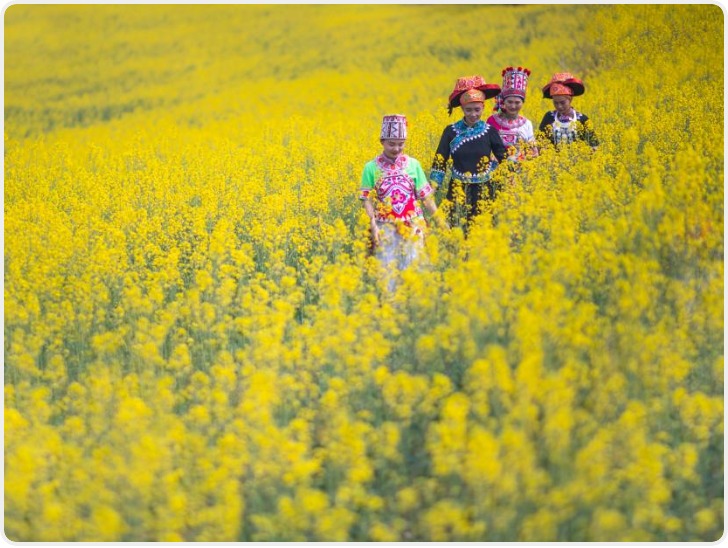树林子像一块面团子,四面都在鼓,鼓了就陷,陷了再鼓;接着就向一边倒,漫地而行;呼地又腾上来了,飘忽不能固定;猛地又扑向另一边去,再也扯不断,忽大忽小,忽聚忽散;已经完全没有方向了。然后一切都在旋,树林子往一处挤,绿似乎被拉长了许多,往上扭,往上扭,落叶冲起一个偌大的蘑菇长在了空中。哗的一声,乱了满天黑点,绿全然又压扁开来,清清楚楚看见了里边的房舍、墙头。
孩子们的手刚送到门缝边,那雪白的纸船如同被一只手猛然抽了一下,霎时间飞出门外,刀片般卷飞到空中后被雨水打上了污点,软塌塌地坠落黏连在地上,再也起不来——雨开始了。
地上像是长了毛。雨水冲刷着原上的泥土,流动起来就混成了泥浆,伴着从干草垛上吹下来的麦秆子,铺在地上就覆盖了原先开垦的路。江湖横流,整块大地似乎都在这暴风雨中战栗瑟缩着。
叶子已不再天上乱窜,老老实实地匍匐在树根下,堆成一团,前俯后仰弓着身子像是在向着大树拜服——乞求着想要回去。树干如同被泼了一层黏糊糊的黑漆,在天昏地暗中隐隐闪着磷光。树枝在这时候变得极有弹性,一屈一伸一摆一停,弹落掉许多水珠,又溅到叶子上。整棵树唯一不动的只有遒劲的根部了,上部狂热的摇摆似乎是要挣脱大地的束缚,最终无能为力,流下一身又一身的汗水。
岸边垂柳的线条沉甸甸的再也舞不起来,像一个在雨中头发淋湿的老妇,含着胸驼着背,哪有起初的那份肆意与张扬。苇塘中的苇子失去了干脆与挺拔,喝醉酒一般瘫软在泥中,连那折断时爆发出的脆响也懒得发出。
葡萄烂在泥地里,还有些残缺的在天上飞,撞上了从电线杆上被打下的湿漉漉的苍蝇,双双消失在泥泞当中。霎时间天上乱成一片——大的,小的;黑的;紫的;活的,死的。一点点一片片挤进视野,又好似要溢出来。
那羊还在有一声没一声地叫唤,人全已无暇顾及。红衫子女孩一手紧紧攥着栅栏木,全身重心向后倒,再一手向前伸去想要抓住门槛。脚下乱了套,布鞋在泥里滑来滑去,腰身也就随着扭啊扭,大花辫子在头上甩啊甩。若不是在这样的天气下,这动作倒是有几分俏皮。左手总算是够着了门框,一龇牙一用力,将身子闪了进门里,带进去一大片水。
老鸟滚爬在地上,泥水浸了半个身子,细密柔软的绒毛此刻蹂躏在一起,整只鸟就好像瘦削了一半。原本鲜艳的黄与土壤混在一起,变得并不那么耀眼了。它竭力地张开两个翅膀,支撑着轻得可怜的身体不要陷到地里去。后爪在湿软的泥中蹬出一道道细小的划痕,却怎么也前进不了。雨水阻塞了鼻息,眼睑已遮住大半,它最后把头向高向远哏了哏,就再也抬不起来。
风不如刚才大了,池塘却像是被几挺机枪扫射着,迸溅出大块大块的水花,狠狠地摔在地上,抑或是打在鱼身上,这带着生命气息的痛苦激起了本已奄奄一息的鱼的求生欲望,奋力收缩起尾巴上的肌肉,拍打着,跳腾着,抽搐着想翻回塘里。
从山上向下望,整块土原都散发着水汽,迷雾缭绕又显着几分硬朗。一切植物、动物,人都朝着一边倒,在自然的力量下鬼斧神工般的和谐。天没有什么颜色,混混沌沌哪怕是一朵乌云也分不出。噼里啪啦——噼里啪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