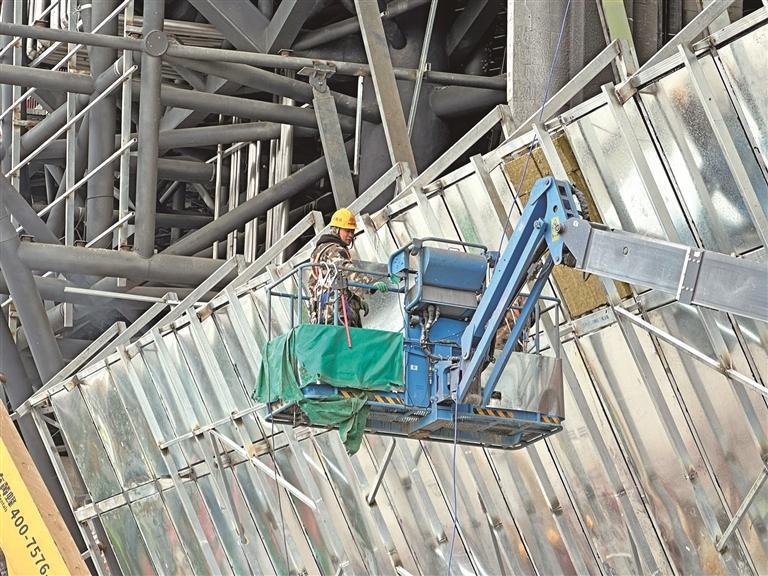“家里没人
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距离邹城市十几公里的山区小村北齐村,原有1500多名村民。随着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900多名村民里,有370多人是60岁以上的老人,大部分独居老人的生活只能依靠互助养老。
对于农村互助集中养老的模式,有人认为这违背了几千年中国农村分散居住的老传统,但现实让农村选择了这样的互助养老。如今,穿过邹城一个个村庄,访客很少能够看到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中青年人,靠子女养老送终的传统,在现实中不得不改变。
在邹城市兴办互助养老院的100多个村庄中,每一位支部书记谈及自己村庄这些年发生的变化,似乎都讲述着一个相似的故事。
“一批批的年轻人离开孩子、老人,远赴城市打工,再后来,孩子也离开了农村。”孙善成说。
在只有电、自来水的家里,每一位独居老人每天从床上爬起来时,在完成一个农民全部自给自足的生活后,要“忘记”自己已经是一个老人了。
在只有120户、450人的康桃村,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80余人。“村里的常住人口只有不到300人,中老年人占了一半多。”村支书康梅青无奈地说。
康梅青和妇联主任每天的任务之一就是在村里转上一圈,对这些空巢老人挨家挨户敲门探望。之所以这样“巡视”,是因为一件事情让他触动很深:村里一位老人的儿女都出去打工了,老人突然发烧,不能动弹,等到村里发现的时候,老人发烧十几天,奄奄一息。
“家里没人,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康梅青说,他的手机半夜里从不敢关机,因为总会有老人半夜找他。
在康桃村党支部的对面,村医务室的大门已经生锈。
“原来村卫生服务站就在村委会门口,村医60多岁,去年得癌症去世了。以前村里人有个小病还有村医,现在生病了只能跑两里路去邻村看。我现在正愁得慌。”康梅青坦言。
实际上,像康桃村这样的小村庄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危机。人都走光了,有的小村已经消失了。
“互助也有
不行的那天”
满玉伦注意到,村里没有年轻人喜欢的网吧、台球室和KTV,老两口担心,总有一天,“第三代”孩子们也要离开这里,到县里上学去,最后村里只剩下一堆“老骨头”。
“如果有一天大家都不行了,最后谁照顾谁呢?”作为养老院里“最年轻”的人,年近60岁的王长喜自问自答,“来到养老院的人不会一天比一天结实,村里如果没有年轻人,互助也不是长事。”
曾有专家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发展设计为四个阶段,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乡镇企业发展、小城镇建设、区域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经过30年发展后,一些农村只完成了四个阶段里的第一步。
“我们在改革农村生产关系的同时,并没有配套改革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致使在集体经济逐渐空壳化的同时,留下了一个公共产品供给的重大制度缺陷。”一位专家表示。
在养老与生存之间,大多数家庭的老人选择牺牲自己,让孩子外出谋生。
然而,子女外出打工并没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相反,村里的老人看到城里子女的周期却越来越长。子嗣的生存与发展,大都摆在长辈的亲情之前。
作为一个60岁的老人,孙善成坦言,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没能留在村里,既不能“养儿防老”,也不能为村里的发展做贡献。在劳动力过早被城市“抽空”的农村,农村的养老和整个农村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实际成了一个问题。
“不把年轻人找回来,互助就后继无人了。”王长喜说。
盘活“空心村”
能不能把年轻人从城里喊回来,每一位农村老人都有自己的思念和苦衷。
作为村支书,孙善成在回忆过去那个村集体的劳动与互助时,另有一番感慨。
“现在这个村庄,其实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集体。现在个人干个人的活,个人打个人的工,个人发个人的财,没有人再考虑村里的发展了,连家里老人都没有时间照顾。”孙善成无奈地说,“过去,农民有土地拴着,现在,土地、老人都拴不住年轻人,咱们村里连个像样的村集体会议都开不起来。”
一位大学时专门研究西方农村发展的邹城市当地民政干部告诉本报记者,现在在一些村里,村集体会议要求30位村民代表出席,实际上,这30个村民代表,一年到头甚至连春节都无法回家凑到一起,更不用说村里平时有什么“政治生活”了。
有专家称,中国农村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社会生态,想要挽救政治、社会、文化以及经济逐渐“老龄化”的办法,就是重新盘活村里剩余的全部资源。
一些有经济头脑的村支书在想,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村的各种资源越来越有集中的可能。现有的“养老公社”也许将成为撬动农民工和土地两个资源的一根“撬棍”。
“反过来想,如果我们把他们的后顾之忧解决了,替他们尽孝了,让老人享福,也算村里给小的们办了一件实事,这也是拴住他们心的一个好法子。”一位当地民政部门干部说。
孙善成书记的想法则更加直接:“有些老人的孩子在外面当领导,当企业家、工头,可以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给村里搞点投资和赞助,上个项目啊,完全可以,这就是老人身上最大的资源,咱不能浪费了社会资源是不是?”
跟孙书记想到一起的还有后瓦村支书王守春。种着大片果园的王守春认为,随着老人被集中起来供养,他们的农田、宅基地都闲置下来了,这对于村集体而言,正是集中起来搞经济的一个好机遇。
“我也想过,把这些闲置的宅基地、农田统一收回来,统一包出去,搞点果园、绿色蔬菜。”
农村问题专家党国英认为,把农民工的父母供养起来,并不能“挽回”外出农民工的心,反而可能让他们更无后顾之忧了。不过,通过自愿的方式,让一些老人手中无力耕种的田地、废弃的宅基地统一使用起来倒是可以盘活农村经济,同时也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养老模式,村集体可以通过收取土地租金,供养村里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