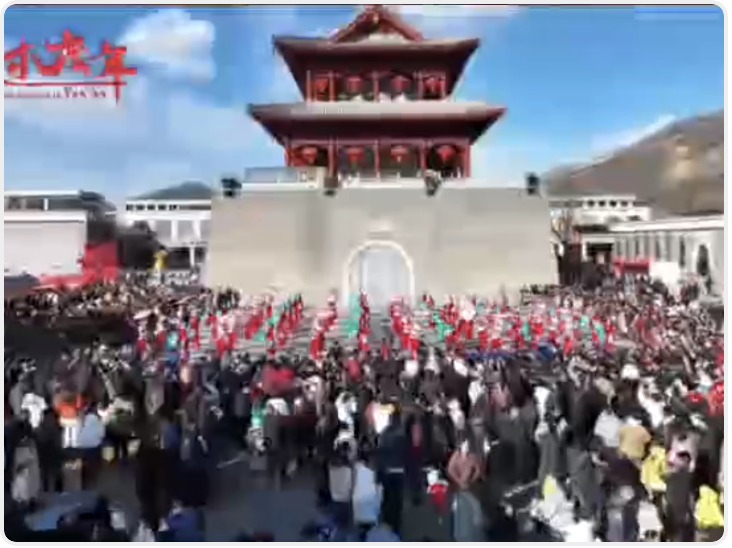反对重刑者:刑法调整不是一味地加刑
对于要求将收买一方像对拐卖一方同样严打的呼声,高铭暄表示反对,“拐卖是重罪,收买是轻罪,不能相同对待”。
“刑法第241条不能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也持同样看法。他表示,他坚持的原因在于对现实公安解救工作的考虑,“其实跟绑架罪最低刑期下调是一样的道理,保护被害人权利,现实中解救工作非常艰难,这是谈判的一个砝码,刑法调整不是一味地加刑。”
支持重刑者:惩罚性荡然无存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王平则持支持态度。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采访时表示,现在来看,这个规定对打击买方市场确实有不利的方面,可以考虑进行适当的修改。只要收买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就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政法大学反对人口贩运国际合作与保护中心主任张志伟表示,很多人也知道收买被拐儿童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是司法事务中绝大部分收买人都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即使被追究也是比较轻微的行政处罚,惩罚性荡然无存,犯罪成本很低,应该尽快加大对拐卖犯罪的刑事处罚力度。
中山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聂立泽认为,对于收买儿童的犯罪行为,处罚应当从严,如果是主动要求人贩子去拐骗孩子,即使出于私自收养的目的,也应当以共谋的共同犯罪论处。聂立泽认为,无论怎样,都不能把人视为商品出卖。
“建议通过立法,加大惩治‘买方市场’。”中国政法大学犯罪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罗大华教授认为,收买被拐儿童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农村。一些乡镇政府、派出所尤其是自治村,甚至还在不同程度地参与到了其中,帮助掩盖事实、上户口等等。“默认也是一种保护和纵容。”
还有研究者指出,《刑法》的规定无形中使收买被拐儿童成了不会被法律追究的“合法行为”。买辆赃车都会被罚款、拘留甚至判刑,可买个大活人的处罚却轻得多,这自然难以从根本上打掉拐卖儿童的地下黑市。
综合央视、《法治周末》等
寻亲者说
记者专访“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发起人张宝艳
被拐家庭多数变故 找到后高兴不起来
也许你不知道,在中国民间有着一支难以计数的寻亲队伍,有的人为了自己的孩子变卖家产,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找;有的人不计报酬,只为了能帮别人找到他们的孩子;有的人为了能让更多人找到孩子,通过网络发起公益组织,长期为之坚持。
今年53岁的吉林通化人张宝艳就是其中一位。她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民间寻子网站之一“宝贝回家”网和“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的发起人。昨日,她在接受华商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这个社会什么都能称为商品,但人不行!即使不知道孩子的真实来源,也不能以抚养和关爱的名义收买儿童。”
“宝贝回家”网站是张宝艳和丈夫在2007年建立起来的,促使她做这件事的原因,是在1992年,4岁的儿子和外婆出游时不慎走散了。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的寻找中,张宝艳心惊胆战。孩子最终找到了,但这件事在张宝艳心中种下一颗种子。2006年,她辞去典当行经理的工作,专职办寻亲网站。2008年,她的志愿者协会成立,至今已拥有全国3万多名志愿者。目前,这个公益组织已帮助772个孩子找到亲生父母。
“772不是简单的统计数字,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一段艰难的寻亲路。”张宝艳记得,2013年,一个叫罗参美的福建女子在他们的帮助下找到了亲人,初来时,罗参美只记得自己被拐时只有五六岁,印象中家附近有座纪念碑,舅舅做榨菜,“我们根据她这些零散的记忆,初步判断是在重庆,就把信息转给重庆志愿者,他们挨家挨户走访。”张宝艳说,找到后才得知,罗的妈妈在她被拐几年后精神失常,父亲已经去世。但当罗参美再次见到妈妈时,妈妈竟然一转头跑到罗爸爸的坟头哭着说,“孩子回来了”。
“找我们寻亲的人有很多,但比较容易成功的,是那些有被拐经历的成年人主动找我们,我们会引导其回忆各种有可能的线索,就像记忆拼图,大致确定区域,然后志愿者再去找。很多家庭在孩子被拐后变化太大,或者过去数十年物是人非,有的因为寻亲债台高筑,有的人找到亲人后,看到破败的家庭,还是选择回到养父母身边,我们高兴不起来。”张宝艳说。
“我非常支持陕西这位全国人大代表的建议,刑法中的有关法条早都该修改了。”张宝艳说,建议公安打拐系统和民政救助系统能联合起来,共同搭建国家统一的反拐信息平台。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由本报特派北京记者陈琳杜鹃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