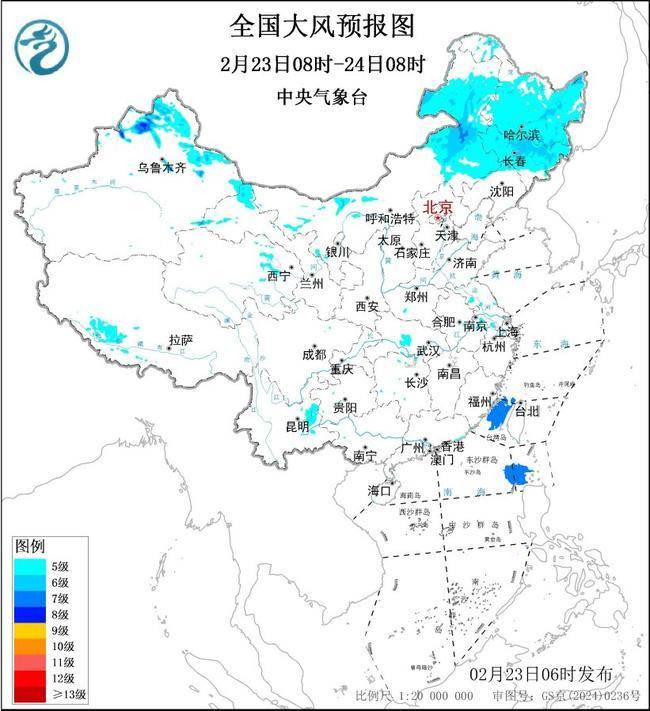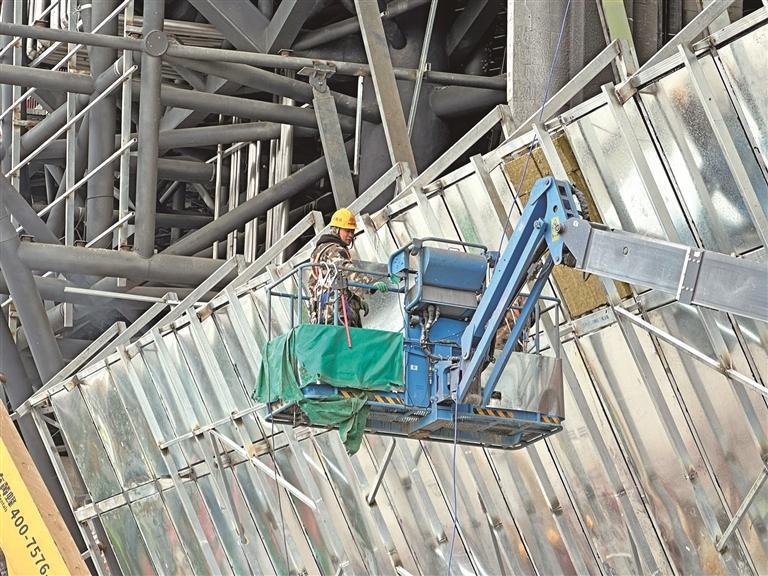在这20起线索来自于举报的案件中,网络举报占了18起,占比90%。另两起则不能确认举报方式。在这18起网络举报中,省部级官员4起,厅级干部14起,分别占比33%和18%,两者加起来占比20%强。也就是说,在5个落马的厅级以上官员中,就有1个是通过网络举报成功的。
网络举报的案件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要么是涉案官员滥用权力,要么是有作风问题,要么是其身份让大家感兴趣,这些特征都有助于在网络上吸引很多人的注意,从而聚拢民意。比如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之子醉酒打人,大家比较关注的点有两个:一是当事人父亲公安局长的身份,二是权力滥用,这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会出于对弱者的同情和对滥权者的憎恨,而对案件给予高度关注。
刘铁男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方面是因其位高权重,对公众有种神秘感,另一方面则是其发生在公众比较敏感的能源领域。此外,就是举报者的身份。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很容易激发公众的想象力。
情妇的举报则把公众的仇官情结与偷窥欲望结合起来,容易在短时间内吸引人的注意力。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选取的分析案例中,出自情妇的网上举报的案件,人气居高不下。
在这些与情妇有关的案例中,纪检部门介入的速度也明显加快:雷政富案第二天介入,同一天证实,第四天免职;单增德案第二天调查,第三天证实,几天后免职;范悦案3天后免职。这种超越常规的处理速度,一方面与纪检机关对短期内聚拢民意的顾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情妇掌握了更可靠的证据。
与情妇举报相比,媒体人举报因为自己非当事人,许多案情是听人转述,加上容易流于主观判断,因而在证据方面存在天然的缺陷,这些需要调查来弥补。
在上述18起网络举报中,有13起是实名举报。在纪检调查越来越向实名举报倾斜的背景下,实名越来越成为网上举报的一个共识。一位研究者整理了从2012年初到2013年8月的28起实名举报,他发现,除了6起正在调查的案件外,另外22起案件的回应率达到86.3%,只有3起没有回应。在19起得到回应的案件中,12位被举报人被免职。
这位研究者还发现,在28位举报人的身份中,有8名商人,6名媒体人,两者加起来占了一半。这说明,在实名举报者的动机中,最重要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商业利益,二是公益。
大量的举报人采用实名,一方面说明举报人的取证意识与能力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也说明反腐生态发生了变化,以至于改变了举报者的预期。在实名与匿名之间,举报者的风险考量也在发生变化,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有两个因素:一是网络的出现,二是纪检机关对于反腐的态度。
网络给反腐生态带来的一个变化是:以前少为外界知晓的反腐案件,现在很难再暗渡陈仓,一个证据确凿的举报在网上公布后,汹涌的民意会不断挤压纪检部门的回旋空间,对其形成压力。另外,实名举报还会把被举报人置于一种受监督的境地,使其起报复之意时有所顾忌。如此一来,实名举报人就拥有了两个对自己有利的因素:一是纪检机关立案的可能性增加;二是被举报人也不敢肆意妄为。这都会大大改变其对举报风险的预期。
不过,当前反腐机制中还缺少一个举报人保护制度,实名举报依然存在风险。
对于纪检机关来说,其长期以来依赖书面举报并拥有巨大的调查裁量权的工作形态或将改变。在很多情况下,它可能不得不抽出很多精力回应网上的举报,这对于其观念和人员的配置都是一个挑战。
信息公开有待加强
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所分析的88个案例处理过程来看,多数案件在纪检部门开始调查时会有一个信息发布,通常的表述是“×××同志因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正在接受组织调查”。
但这一信息发布的时间因个案有所差异。从总体上说,在网上关注较多的案件,公布的时间较为及时;而公众不太关注的案件,则纪检部门公布信息的紧迫感不够。
刘铁男案则是个例外。2012年12月6日,媒体人罗昌平通过微博实名举报刘铁男。当天下午,国家能源局新闻办公室回应称罗造谣,并表示将报警处理。此后,刘铁男一直以能源局局长身份参加各种活动。
2013年1月30日,罗昌平在微博上称,中央有关部门已就其实名举报一事立案调查。他后来澄清说,这是自己的“以诈施压”术,希望能以此推动调查进程。
2013年3月,刘铁男在新一轮机构整合中落选国家能源局局长,但留任发改委副主任。到了2013年5月12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信息称,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从罗昌平实名举报到中纪委宣布调查,耗时5个多月。罗昌平说,他在这一过程中“备受煎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88个案件标本发现,在所有的线索来源中,情妇实名举报信息公开的速度最快——不仅开始调查时公布,立案时公布,在调查的各个阶段也有公布。媒体人的实名举报速度则次之。
此外,在信息公开的速度上,网上举报相对于传统举报要快一些,实名举报相对于匿名举报要快一些。由此可得出结论:纪检部门信息公开的速度,与其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成正比。
相对于开始调查时的信息公开,纪检部门调查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则更为欠缺。《中国新闻周刊》搜集的88个案例中,在纪委的调查阶段,通常是只在开始调查时公开一次,此后再无消息。
这是个漫长的、沉默的调查过程,给了各种传言充分的传播空间。李春城在2012年12月2日被带走,12月6日新华社发布了“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此后又在2013年1月19日中纪委的一次发布会上宣布立案,此后的9个多月再无消息。在这一过程中,不论是在四川官场还是在网上,都流传着各色版本的传言,包括许多种版本的“官商勾结”,还有许多版本的“官官勾结”。在案件的结果最终公布之前,民众已经从这些传言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这样一来,相关部门等于把最大的一块舆论阵地,客观上让给了传言。
在网络传播的背景下,纪检机关应该改变过去关门办案的观念,建立一种阶段性公开的机制——在案件调查的各个节骨眼上,比如带走、立案、移交司法等环节,除非确需保密,应尽量给民众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