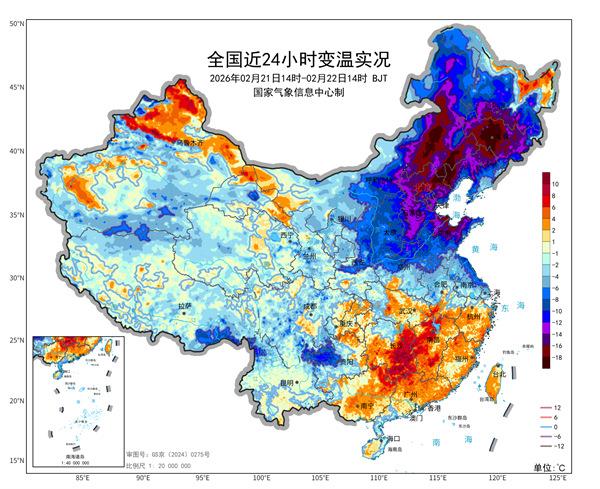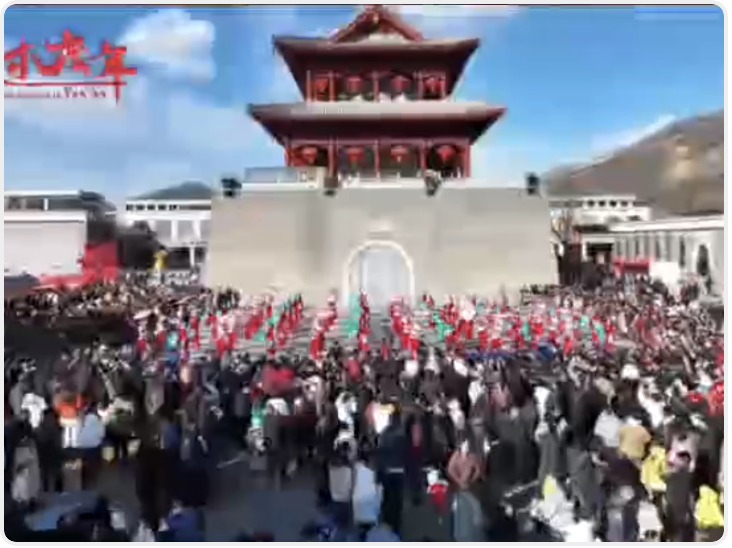一位山沟里的乡村小学老师,在偶然与曾为“慰安妇”的老人相遇之后,便走上了一条艰难的调查、诉讼之路。他表示,自己希望能拥有更多的中国同行者。
2013年9月4日凌晨,“中国实名控诉侵华日军性侵第一人”万爱花在山西太原住处去世,享年84岁。
老人的葬礼,由山西退休乡村教师张双兵主持。
在很多曾为“慰安妇”的老人心里,张双兵是最能信任的人。包括万爱花在内的16位老人,曾拖着孱弱的身体,在他的带领下远赴日本出庭。
张双兵今年60岁,山西省盂县西潘乡羊泉村人。1992年,他亲自写下并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份侵华日军性侵控诉书。随后,一场长达15年的跨国诉讼展开。
在山西,张双兵走访了123位老人,并将她们的经历著书,编写成中国第一部慰安妇口述史书籍——《炮楼里的女人》。
他因此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
30年时间里,为了给老人争取应得的尊严和必要的生活保障,张双兵四处奔波,背上了十几万元的外债,同时也牺牲了自己和妻子的健康。
在与法治周末记者的通话中,张双兵经常叹气。对于自己所做的“这件事情”,对于沉重的人生,他感到无奈而无力。
“偶然间,把不该担的责任担起来了。”他说。
如今,张双兵希望能够有人和他一起“扛起责任”。不过,即使没有人与他并肩,他依然表示自己想要坚持下去。“半途而废,对老人,我交代不了,也对不起我自己。”
20年“慰安妇”民间调查
“今年就走了4位老人。”张双兵叹口气道。明年,已内退5年的他即将正式办理退休手续。
从而立到古稀,这位住所离县城60多公里的乡村小学教师,一直在为“慰安妇”们奔走呼号。
如今,张双兵依然坚持每月至少看望两次老人。他微薄的工资,几乎都花在了车费和接济老人的生活上。“家人基本支持我,但有时涉及到花销,也会生气。”他说。
31年前一个深秋的下午,命运让他与慰安妇有了交集。
那个下午,在带领学生劳动后的归途,他看见一位老妇跪在地上收庄稼。惊呆之余,他忙问学生:“老人是谁?”
学生答:“她叫侯冬娥,是河东的‘五保户’。年轻时,因为长得漂亮,人们都叫她‘盖山西’,她的老汉是个半身不遂。”
交谈后,张双兵和学生帮侯冬娥割完了地。老妇跪在张双兵面前,头贴着地,一个劲儿地念叨:“可遇上好人了,可遇上好人了……”
从那时起,张双兵对这位老妇留意起来。随后,他听说了侯冬娥曾为“慰安妇”的经历。
10年后的1992年6月,张双兵在《山西日报》上看到一篇转载华岗劳工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报道。报道中提及,中国受害者,包括劳工和“慰安妇”,都可以向日索赔,希望受害者能够站出来。
张双兵拿着报纸,首先找到侯冬娥,再次希望能询问出老人过去的经历。有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去候冬娥家说服老人。在探访的第十天,侯冬娥大哭了一场,将那段“实在不愿意提”的经历,讲给了张双兵。
此后,与他同村的刘面焕、冯转香、万爱花等老人,也对他讲出了深藏心底四十多年的伤痛。
为了保留这些“活的证据”,张双兵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对“慰安妇”的悲惨历史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搜集和整理。仅在山西,他就走访了123位老人。
当时,交通并不发达。张双兵要去的大多数地方没有交通工具。靠着两条腿和自行车,他走遍了山西的盂县、阳曲、太原、武乡、沁县以及河北的平山县。一年夏天,在完成走访后回家的路上,他差点儿被洪水冲走。
一开始,张双兵想过,要在全国大范围进行调查,“然后进行大范围的受害赔偿,清理侵华日军罪行”。但限于个人能力,他至今没能走到那一步。
回顾这个漫长的过程,张双兵又叹了口气说:“我在山沟里,各方面条件差,用的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电脑。我工作了40年,为了做(“慰安妇”调查)这个事情,还耽误了工作,工资也调不上去。”
同样关注“慰安妇”群体的志愿者刘炜,曾在个人博客写下张双兵的遭遇:在调查“慰安妇”群体后,有人来“找麻烦”,导致他的妻子因受惊吓而变得神智恍惚,至今未愈。
如今,张双兵走访的大多数老人都已离世,在世的只剩二十几位。
对于“若老人们都走了怎么办”的问题,张双兵早就想过。“我会和律师提前安排,让老人和儿女谈话。老人让儿女跟着我,继续跟日本政府斗争下去。”他说。
15年跨国民间索赔
1992年7月8日,《参考消息》刊文《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首次向日本索赔》。其中提到的“中国大陆受害女性递给日本政府的第一份控诉书”,出自张双兵之手。
张双兵用了10天时间,将老人们的哭诉整理出来,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给日本政府,并提出每人10万元人民币的索赔。
“一开始想得很简单,《参考消息》报了出来,我以为日本政府会给老人答复。之后,我们非常压抑地等了一年,以为会有人来调查核实,但还是没有回答。到了1993年10月,我想,既然日本政府不回答,那就打官司吧。”他回忆道。
相对于日本政府的毫无回应,控诉书却引起了日本一个民间律师团和支援团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