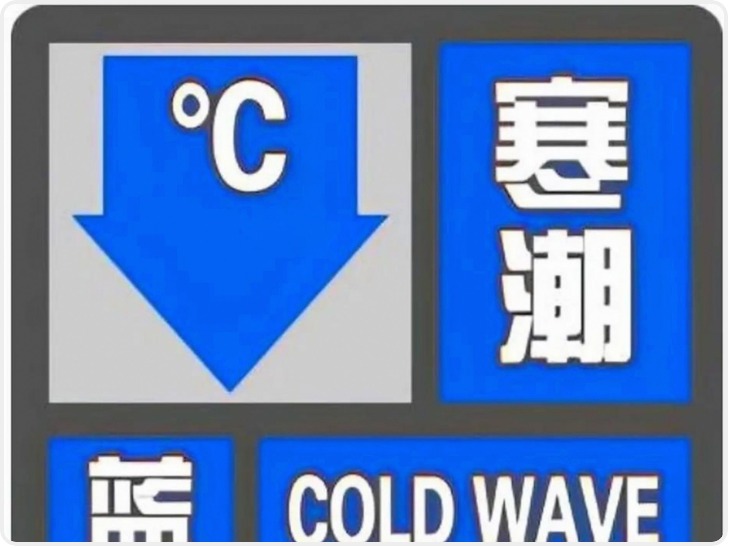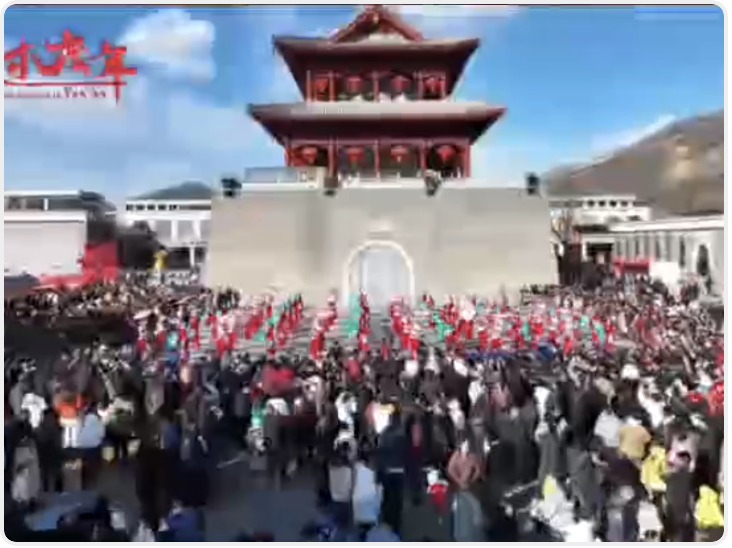接受我采访的原积水潭医院产科主任李少芬说,胎儿成形的第28周,即应当计入我国人口中,“是一个人了”,应该得到“人”的待遇。但富平县的婴儿们显然没得到。
2013年年末的一次电话回访,更是让我脊背发凉——如果命运重新给这些家长一次机会,他们会重新选择吗?答案是,不。
重来一次的机会不是我假想的,而是公安机关给的。
从去年8月开始,越来越多的家长作出了响应,他们意识到当年被张淑侠以同样的手段骗去了孩子,纷纷向公安机关报案。最终,当地警方部分予以立案并侦查破获。我致电富平县唐凯一家,询问他家的案子进展怎样,答复是没被立案。他说,他们家不准备再继续找孩子了。理由是:据他了解,县里有几户人家的孩子被找回来了,但发现孩子确实有残疾后,就又放弃了。我追问,再放弃以后送到哪里?他说,可能是福利院吧。“但是据说福利院也不愿意收,所以孩子找回来以后也很麻烦,所以他不找了。
他还说,还有一些丢了孩子的家长,一听说找回来的孩子确实有残疾或疾病,都纷纷打消了继续报案寻找的念头。唐凯还对我细算了一遍,照顾一个残疾孩子将给一个农村家庭带来多么大的负担。
农村的经济状况当然是放弃坚持的原因,另外福利机构所能提供的依托、民政制度上的完善,都有待于继续讨论。否则,这些孩子们作为“人”的价值将继续轻易地湮没在环境压迫之下。
如何建立合法的领养渠道
至于“放弃”孩子以后送去哪里,我在今年的采访中倒是有一些见闻。
在徐州贩婴案里,我看到了家长放弃孩子后送给人贩子的后果。之所以关注这个选题,是因为在之前的消息里看到一句:徐州铁路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拐卖儿童案,但是在解救出孩子后,家长不愿来认领。
前去调查后发现,这些孩子都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办案民警说,当地的孩子像被牛羊一样放养着,人贩子抓住机会劝说这些家庭送出了健康的孩子。这些山区里的家庭贫寒之极,年收入只有两三千元,卖一个孩子顶上一家人十年的收入;如果孩子被送回去,他们就得退钱。所以这些父母不愿来徐州接孩子,甚至在民警前去调查时都没有一人肯露面。
但像物品一样被父母卖走的孩子们,在东部地区却得到了宝贝般的待遇。同时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被拐卖的孩子又很难被当地福利院接收。于是,费力解救出的孩子只能留在收买人的家庭里,而且貌似还是最好的结果,这让办案民警很是困惑。有人说这个案子的启示在于:能不能在不同区域间建立起合法的领养渠道,在制度上理顺这个目前存在的人口困局?
我所经历的另一起放弃孩子的选题,是对“弃婴岛”的探访。石家庄市早在两年前引入了这一设施,随后引来了争议:是不是变相鼓励父母弃婴?福利院方面解释了庇护弃婴的初衷。同时我了解到,这些家长们在扔孩子时都如惊弓之鸟般的窘迫,由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的压力,弃婴者们常年与工作人员们玩着猫鼠游戏。工作人员感慨,但凡有办法,他们也不愿扔了自己身患残疾的孩子。
再又回到富平县医生贩婴案上,怎样才能避免亲生父母割舍骨肉的悲剧再上演?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启示:国家民政系统能不能给这些先天残疾的儿童家里予以补贴,通过在经济上减轻压力的方式,避免孩子被遗弃后产生种种问题?
在石家庄采访的时候我才得知:有缺陷的孩子进入福利院,是再难有机会被收养家庭领走的。我想,和富平县的新生儿、徐州的被拐儿童一样,既然这些孩子们没有选择的权利,那么怎样在制度上引导他们的家人作出更好的选择,可能是我们的社会在未来要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