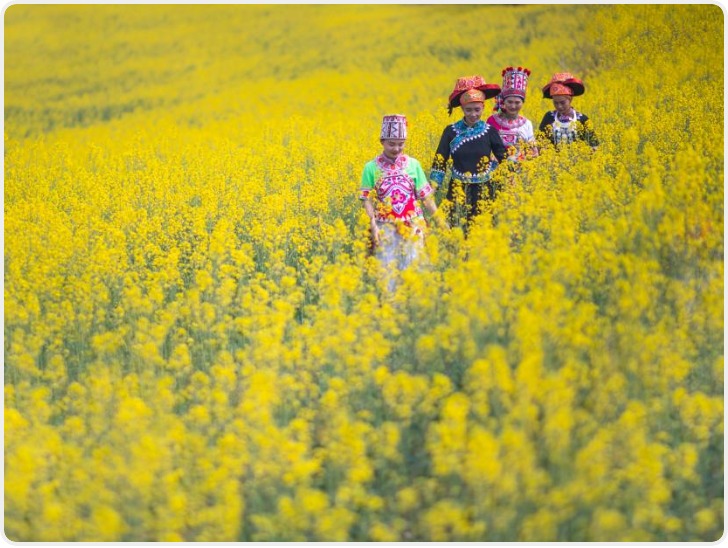在年文化中,不光有日常琐碎的细节禁忌,还有对天与地、风与雨、山川河流的敬仰……在旧时,一些政治家就利用人们对天地的敬畏,将天意与民意联结起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意自我民意”,并通过自然灾异现象来警示帝王,权力的神圣性与责任感,就通过对天地的信仰维系在一起。过年时的种种礼俗与禁忌,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文化的重申与加强。
封建时代,祭祀天地是由皇家所垄断,民间社会只能祭祀与生活有关的“小神”,让小神去天上通大神,譬如小年祭灶神,是让灶王爷吃香的喝辣的,年夜升天见天上玉皇大帝时,就会替自己家美言降福。不仅要祭神,还要驱魔,燃放鞭炮源于古代的燃烧竹筒,用以驱逐恶魔厉鬼。不少曾经的过年仪式,如今逐渐淡化了原义,在生活中被艺术化,成了传统文化的符号,留存在民族的记忆里。
在民间,过年的禁忌是“十里不同俗”,如果细究的话,都包含着一些朴素的观念在里面。比如有些地方正月禁止砍伐树木,不可捣毁鸟巢、掏取鸟蛋,不可杀害幼虫,以及未出生的或刚出生的动物,还有过年这一月不可动土、不可修建城郭。这些体现的都是传统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意识。我们的祖先明白“天人合一”,对自然的保护其实是对人类自身的保护,也就是现在时髦说法中的“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如信仰一般的过年礼仪,正慢慢卸载了其神圣价值,一些祭祀活动已经由一些民间表演活动所替代。我们也不再敬畏天地,民间的宗祠已越来越少,只有一些对先人的纪念活动,却不再是礼教行为,而仅仅是一份基于传统形式的纪念行为。
如果没有“年”,乡愁何所依
过年成了一种顽强的存在。当我们被一个没有明确解释的缘由驱动着去踏上归乡之路时,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说春节就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或许有失偏颇,但春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所体现出的强大力量,确实和其他信仰的驱动力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看重过年,也就是看重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也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延续。曾经有一位国外汉学家说“中国人只要还在意过春节和家庭团聚,中国文化就仍然根基牢固”。
春节所承载的习俗,当然也不全是精华,可能还有不少属于糟粕。于是,近现代以来,为了改变曾经的积贫积弱,甚至从国家的层面推动废除近年这种风俗的努力,结果却无功而返。1928年5月7日,中华民国内政部呈国民政府,要求“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1930年,政府重申:“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甚至乡间售卖历本的小贩,亦一并捉去拘役,一时间人心惶惶。不过这种做法,一二年后即消失,人们照旧过自己的春节,当局也无可奈何。1934年,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要求“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
于是这个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就这样顽强地延续下来。有人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春节,认为人们之所以把过年看得如此重要,主要的原因是,回家过年,可以滋养对生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快节奏多变化的社会,人们更需要这样的感觉,来给自己一个确切的定位,并在这种感受中康复受伤的心灵。这看起来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但又好像不全是。
我们必须承认,包饺子、贴春联、祭祖、吃年夜饭、拜年、发红包等一系列习俗,是镶嵌在中华民族潜意识中的文化元素,无论走到哪里,身居何处,这些奇妙而有魔力的元素都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永远都不可替代。
我们也必须承认,很多习俗的改变是对社会发展的适应,但不能在形式变化的同时,把习俗中的文化元素和心理需要也同时置换掉了。
传统中国人追求在天地间安身立命,如何通过春节找寻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精神寄托与信仰,是在我们提出文化复兴的今天可以思考的话题。如果缺乏了人们因年节而派生出来,对天地的信仰与敬畏,对过年这种人格化的崇敬,那么我们的灵魂里还有什么呢?我们作为中国人的标志是不是因此而弱化?我们的乡愁又何所归依?